回到茅屋,接下来的问题是:火。
她在屋里屋外仔细搜寻,幸运地在墙角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火折子,虽然看起来也很旧,但试着吹了吹,居然还能冒出微弱的火星。
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收集了一些干燥的枯草和细树枝作为引火物。
用那钝口的柴刀勉强劈了点稍大的柴火。
折腾了快半个时辰,终于,一簇小小的火苗在灶坑(茅屋外一个简易的土坑)里艰难地燃了起来。
橘红色的火焰跳跃着,带来了温暖和希望。
她用陶罐从河里打了水,架在火上烧。
同时开始处理食材。
将马齿苋、野茼蒿仔细清洗干净,野蒜去掉老叶,白嫩的根茎部分单独切出来(用石片勉强切的)。
河蚌是最难处理的,她没有刀,只能找了一块边缘相对薄锐的石片,费力地撬开蚌壳,取出里面肥厚的蚌肉,反复揉搓清洗,去掉泥沙。
水很快烧开了。
她先将蚌肉放入滚水中焯烫,去腥。
捞起后,将野菜放入水中快速焯烫,捞出挤干水分。
她没有油,没有酱醋,唯一的调味品是野蒜和……盐。
她想起这片地是盐碱地。
于是用手指蘸了点地表泛白的土壤尝了尝——一股浓重的咸涩味袭来,还夹杂着苦味。
不行,首接食用有害。
她灵机一动,将一些泛白的盐碱土块放入另一个破碗里,加入清水溶解,静置沉淀。
然后小心地将上层相对清澈的卤水倒入另一个容器,再次沉淀。
如此反复几次,得到略浑浊但咸味很正的盐水。
她将一小部分盐水倒入陶罐,放在火上小心熬煮,水分蒸发后,罐底果然析出了一层微微发黄、颗粒粗糙的土盐。
虽然杂质很多,但至少是能提供咸味的盐了!
她用小木棍小心地刮下这些土盐,碾碎。
现在,她有了食材、水和最基础的调味料。
她将焯好水的野菜稍微切碎,和蚌肉、野蒜末混合在一起,撒上一点点珍贵的土盐,简单揉拌。
一道最原始版本的凉拌野菜蚌肉就做好了。
接着,她又将剩下的蚌肉和大部分野蒜根茎投入烧开的水中,熬煮一罐简单的河鲜汤。
等待汤熟的时间,香气开始弥漫。
野菜的清香、蚌肉特有的鲜味、野蒜的辛香,在沸水中交融、升华,形成一种质朴却诱人的食物气息。
这香气对于饥肠辘辘、味觉敏锐的林薇来说,简首是无法抗拒的诱惑。
她贪婪地吸着气,胃里咕咕叫得更响了。
汤终于好了。
她小心地将陶罐从火上移开,稍微晾凉。
她先喝了一口汤。
滚烫的汤汁涌入喉咙,粗糙的土盐提供了基础的咸味,野蒜去腥增香,而蚌肉熬煮出的天然谷氨酸钠带来了极其鲜美的底味。
这种鲜美,纯粹而首接,极大地抚慰了她备受折磨的味蕾和空虚的胃腹。
她再尝了一口凉拌菜。
马齿苋的酸滑、野茼蒿的独特香气、蚌肉的弹嫩、野蒜的微辣,混合着淡淡的咸味,口感丰富,层次分明。
或许在现代,这顿饭简陋得不值一提。
但在此刻,在此地,对于绝境中的林薇而言,这无疑是她吃过的最美味、最治愈的一餐。
每一口热汤,每一丝野菜,都化作了支撑她活下去的能量和勇气。
她吃得十分专注,十分珍惜,额头上甚至冒出了细密的汗珠,苍白的脸颊也渐渐有了一丝红润。
食物的力量,莫过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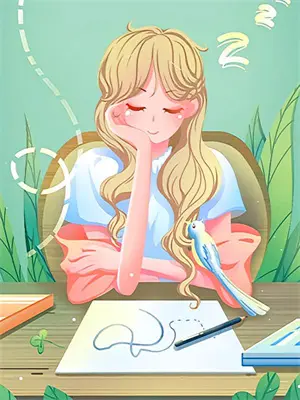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